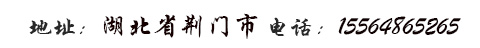金重纪念同树才一起的岁月
|
多少年来,我一直惦记着树才。总是问他的后脑勺是否真得被掀掉了一大块儿。明明知道这是他诗中的一句谎言,却因年复一年岁月的流失而变得忧心忡忡。年秋,他带着重感冒来到柳巷胡同向我告别而离开北京,到非洲一去就是4年。等他撇下亲手种植的面包树和芒果树回到北京时,我已经因再也忍受不了寂寞和孤独而去了异国他乡。 (金重粉棒画《鱼系列》;下同) 乞丐 我是于年12月与树才相识的。当时我初到北京外国语学院,听说当时校园中有三个才气横溢的人:英语系的晓丹,西班牙语系的黄康益(老康),还有法语系的陈树才。被我对文学艺术的狂热所打动,我的同班同学王伟庆(少况)同意为我一一引见。那天晚间我进到树才的宿舍时,他正趴在他的二层铺上写着什么,看我站着同他打招呼,马上说:坐下吧。我说:站着好,离你更近。树才轻轻地鼓起掌来,会心地笑了。第二年,树才放弃了校园和校园“泰思”文学的编辑工作,去了一家离北外非常遥远的贸易公司。这从此打开了我寻找他的艰难历程:每次去看他,都要花上一天的行程。最可怕的,就是那座安定门桥。每次上坡把自行车骑上这个立交桥头,我肯定会断了气。再坐到石头台上,把怨气攒满,等着见到树才时全都撒在他的头上。可一到公司的大铁门口,我会马上被拦住。打量我披散着长发,落满灰尘的脸,穿制服的门卫说:不许进!当得知树才在“生病”而没上班,我又到他的宿舍找。他居然住在第十四层!这一次他太高了——我是没法站着同他讲话,也没力气去爬那象巴别塔一般的楼梯。陈——!树——!才——!我咬准每一个字,高声地喊了起来。他出现了,在那高高的,象小火柴盒大小的阳台上。“我的爱人站在高楼伸出的嘴唇上......”我马上想起了他几天前寄给我的诗,于是喊道:“快下来救我!我快被人海淹死了!”到了深夜,树才提出要同我回北外,我说:你没自行车,怎么同我走?他说:坐末班车!末班车象是一个孤独的灵魂,它卸掉了一整天的喧嚣,在卸去了一整天喧嚣的大街上奔跑。树才抱着一个毯子圈儿,就象是坐在这车中的一个乞丐,寻找着这一天的最后归宿。我用尽双腿所有的力气,把自行车骑得飞快,一站一站追逐着这辆末班车。每当汽车到站停下,我便从后边追上向车里挥手。我是这城市中速度最快的流浪者。树才是一个离不开校园生活的人,我那时真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把自己与校园割开,跑到公司里去天天同与他一点都不相干的人打交道。那里的生活令他发疯,叫他变得玩世不恭,再加上法国文学对他的天生浸泡,他就更玩世不恭,并尖刻无比。在非洲时,上司每天都会对树才说:小陈,好好干。直到有一天树才对他讲:再好好干,不也就到你那位置吗?也许真的是因为干得好,回到北京后,公司马上决定“提拔”他当处长。你们决定?为什么你们决定我?为了表示抗议和反对,也不顾一个爱他的姑娘的极力劝阻,第二天上班,树才的头掀掉了一大层,成了秃头。陈树才,看样子你的脑袋真有问题啊。领导说。难道你愿意当乞丐不成?流浪者 而对我来讲,校园的生活也不是象梦想中的那样长久。年深秋,由于生活上彻底的拮据,我把书籍和一些杂志寄放在王伟庆那里,对树才不辞而别,结束在京城的流浪,回到故乡松花江边的一间小木屋里。那时冬天的暴风雪如期而至,仿佛把我隔离在了一个世界的尽端。我来到一座教堂,思念着每一位朋友,我写下:圣歌,从圣坛响起 令我谦卑的,是我心会的语言 上帝,我灵魂中的泪,是真的 ——你会相信 树才终于听到了我的声音,并回了我的信,那是两首我看到的90年代中国诗坛上最早出现的诗:一月。沉甸甸的心被笛子伤透茫茫心事禁不住泪水的打击一月。一天细雨,夹着一天雪道路发霉,枯草陷入泥泞在北外的时候,我经常搬两把椅子,在周末的深夜躲在走廊的尽头同树才谈诗。我们曾谈过中国诗歌在90年代将是什么样的走向。但我没有料到树才的诗,会变得如此地绝望和悲痛:二月。孤寂的手在书中摸索在无法把握的咳声中寻求健康二月。一个乞丐,怀着孤寂的心仰望童年,泪流满面对于他,“历史”就如同是一个“不眠之夜”,驱使他离开这城市:我看到,城市像雪团往外滚猛一回头,内心像永诀一样无情读着这“一月”和“二月”的诗,我一下子流浪到了大兴安岭脚下的一个小镇上。午夜的火车,摇晃着这个小客栈,大雪,已埋住了半截窗户。在回哈尔滨的途中,我的书包被突然蹬上火车的劫匪抢走,里边有树才的诗,我的草稿,画笔,和仅有的十元人民币。到站后,看到爸爸和妈妈来接我时的眼色,我仿佛觉得是要被法庭审判一般:我们供你上名牌大学好找一个好工作,你为啥要选择流浪? 他们的脸上充满了一种带有决心的愤怒,就象在我十八岁那年,发现我失去贞操时一模一样。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北京 我没有有意选择流浪啊。我决定再回到北京,去看树才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我要再回到外语学院的绿长椅上,去妄想某个陌生女孩,会突然走过来,坐在我的身边......画家许仲敏常对我讲:艺术家卖自己的作品,会象卖孩子一样难过。我不知卖孩子是什么滋味,但为了攒钱回北京而卖掉我的那幅“掠过北京的影子”,我感到和失去情人一样心痛。而树才说:我不还是那个样子吗?带你去吃烤鸭吧。在安定门,有一家向南开门的烤鸭店,我和树才坐在窗边的位置,望着这安定门,别提我有多高兴了。树才读了我印的《一品红日记》,总结道:郭钟的诗,都是“爱情诗”。这下我完了,我心想。一阵零星的鞭炮声在窗外响起,树才和一些孩子混在节日的人群里。多么熟悉的声音。小的时候一到放冬假,我就盼望着春节的到来。每一次爸爸都会背着妈妈给我买最贵的焰火盒。我对那火药的爆炸声,和五光十色的焰火着了迷。到了春节,当着满屋的亲朋好友,妈妈问我:小四儿,长大了当什么?大家马上七嘴八舌地插了进来:当大夫,像爸爸。当警察叔叔。不,当解放军叔叔!我想了半天,突然说:做鞭炮。我喜欢火药!窗外的鞭炮声继续响着,并且越来越近,突然间,变成了机枪声,子弹破窗而入,一个个在墙上电花一样爆开!我一下从睡梦中惊醒,从床上跌到地上。树才,树才!我强忍着膝盖的剧痛冲出房门,骑上自行车跌跌撞撞地在布满碎石和砖块的大道上穿行,慌张的人们四散奔逃,有些被人抬着,一个姑娘躺在马拉的木板车上,整个上身鲜血淋淋。我跑上前去,认出了她穿的那件印第安人特有的黄色皮裙。难道是她?“小兰,小兰!”我拼命地喊着。这时,远处又有一队战车开来,带着铁甲和头盔的武士,继续向人群发射铁箭。一支箭从一颗树上穿过,立时留下一个圆孔,另一支箭击中我的自行车前胎,我从车上摔到了这棵树下。这时一辆战车呼啸驶来,当场将一个孕妇和一个头戴羽毛的印第安小孩压在车下。加利福尼亚共和国的冬季午夜,来自太平洋的暴风雨席卷着棕榈,狂暴地冲打着这个废仓库的瓦楞铁皮墙。我独自在用纸箱子搭成的床上坐着,闪电一次次照亮我的脸。我怎么也无法挥去刚才那个噩梦。那台旧式的木壳电视中,一部屠杀印第安人的电影不知何时已经演完,频道没有了信号,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我坐到窗前,望着外边仅有的一盏路灯,对自己暗语:是梦,我这不是醒着吗?我这不是还活着吗?梦过去了。海鸥,在远处的空中叫着,象是在呼唤同伴。浓雾笼罩的早晨,看不到蓝天,大海,也看不到太阳。我来到南加州大学门外,在宽大的台阶上坐下,观看着陆续来上课的学生们。这时,我已饥饿不堪。忽然,一个女孩停在了我的面前,问我:“AREYOUOK?”我站起身来:“啊,没事。我没事。”她又问:“你从中国来吗?”“是”。“我爸爸妈妈也是中国人,”女孩接着说:“听说北京非常美丽,有美丽的林荫大道长安街,颐和园,古老的胡同,四合院......”“是”,我说:“非常的美丽......”姑娘随手递过来一袋儿甜面包圈:“我没动,你要饿了就吃吧。”我马上接了过来,问:“请问姑娘叫什么名?”“噢——AMY,妈妈叫我小兰。”象一只海鸥一样,树才的信再一次找到了我,从塞内加尔的天涯海角,神奇地落到我的手中。又是一叠厚厚的诗稿,我把它从领口揣进怀里。在校园出口的地方,有几个穿制服的人在发书刊。我上前拿了一本,是美国简史,翻开第一页,头一句话是:美国的发展史就是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。“拿一本吧,免费的”,一个高大和蔼的年轻人说。我伸出手同他握手:“谢谢,我有礼物送给朋友了。”辽阔的太平洋上,太阳已经升起。骤起的大风吹乱了我的长发和灰色的风衣,我拿出笔写下来到加州共和国的第一首诗:《一月圣迭歌》。我的前方,是一条陌生的,长长的婉转下山的路,我慢慢向前走着,空中响起了小兰的话语:他,是上帝用光线制成,因此任何铁栏,牢笼都无法将他紧闭。他的名字,叫自由天使。金重,美国圣地亚哥,-版权所有 金重简介 新九叶诗人之一,译者,艺术家,年生于哈尔滨。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,获硕士文凭。年移民美国。现为幸存者村庄书局主编。金重诗集:《雪不在乎》。主要英译汉作品:布罗茨基,塞克斯顿,狄金森,金子美玲。主要汉译英作品:《大篷车,中国当代诗选》,《冬至,中国诗人40家》,《嘴唇开花,梁平诗集》,《还给我们泪水,指纹诗选》。 其它近作 大瀑布|金重《安妮?塞克斯顿》(外1首) 狄金森:最遥远的花朵(外7首) 金重译 我巨大的悲伤和年龄无关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yipinhonga.com/yphjz/9861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花市添喜气花样迎新春梅州第36届迎春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