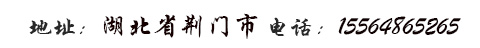桑榆文学周刊第期文苑撷萃陈晓君
|
桑榆文学周刊第期文苑撷萃编者按 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年8月长春老年大学现代文写作班一群志同道合、热爱文学的文友组建了深受中老年文友喜爱的桑榆文学社,至今已由当初的十几个人,发展到如今的二百余人,会员来自全国各地。共有国家及省市作协会员百余人。其中:中国作协会员8人;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30余人,经文学社自己培养推荐的有8人;长春市作家协会会员百余人,经文学社自己培养推荐的近90人。经过三年多的淬炼,文友们的写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,很多文友的作品纷纷在国家、省、市各级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发表。大部分作品还获得了省市文学竞赛大奖,极大地提高了桑榆文学社的知名度。经社委会研究决定从桑榆文学平台期起设立专栏,展示省、市作协一会员在省、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己经发表的优秀作品及各类大赛中的获奖作品。本期推出的是长春市作家协会会员陈晓君的作品。请欣赏。 陈晓君诗文选作者简介陈晓君,长春作家协会会员,公主岭市作家协会会员,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有诗词,小小说,散文等发表在省内外报刊,并·有作品在省内外征文中获奖。 陈晓君诗文选散文·中秋夜听雨 今夜我所居住的城市下雨了。雨夜很寻常,若非说不寻常,那便是在这雨夜里过中秋,在中秋里听雨会不会听到一些别样的窃窃私语呢? 中秋节意味着团圆。而圆月恒古以来便是团圆的象征,尤其八月十五若不见圆月,人们喝酒的兴致多少会减去几分,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大诗人李白可以携着影子对着明月畅饮,他之所以在这万家团圆夜里还能兴致勃勃,没有被思念所烦恼,是因为有一轮皎洁的明月相伴,对于浪漫的诗人也许这就足够了。因为他知道人生不可贪求太多。一刻清明,一刻享有便是富足。月有阴晴圆缺,缺失的那部分难道就不美吗?缺失也是一种美,没有缺失,没有遗憾,何来圆满一说呢! 中国人给月亮赋予了太多的美好,太多的希望,太多的传说。在这中秋佳节里,多少痴儿黄瓜架下等看广寒宫里遥望家乡的嫦娥,伐树不息的吴刚,还有那只尽职尽责的捣药玉兔。可是这一切,只因一场雨,一年的企盼便落空。他们也许遗憾吧,我真想告诉他们,那就静下心来听听雨吧,中秋夜里的雨一定别有滋味。 也许是脑海里积压太多的喧嚣,身体被人流碰撞得疲惫,总之我爱上了听雨,不知何时,不知何地,爱就爱吧,管它何时何地? 在陋室的窗前,手捧半杯清茶,闭上眼帘,听窗外时急时缓的雨声,脑海里盈满缓慢滴落的雨滴。圆且胖的杨树叶急促地抖动,亮晶晶绿油油,一滴、两滴、一串串、一条条任那雨千丝万缕随意飘落。那叶就在这里默然承接,即便瞬间回归尘土,那又怎样呢?你来过,我爱过。 如果雨下在夜里,绝不在灯下听雨。灯光虽暗,也会打扰你的思绪。最好的方式就是关掉灯,静静地窝在被子里,听那雨滴落在灰瓦楞上化作无数颗后再落下,细细碎碎,就如离人的眼泪;那雨若落到草叶间,便要经历一段长长的旅程,再“啪”的一声回归尘土。漫天的雨丝毫无章法地下着,大地瞬间成溪,成河。心里的雨滴却一滴一滴有条不紊地滴落着。 余光中说“这雨从宋朝一直下到今天。”我想说这雨从这里一直下到远方,下到缘起的地方,下到枯枝生出嫩芽,下到思念成海,下到心事成昨。“莫愁遮断山河影,照出山河影更愁。”清朝诗人樊增祥中秋夜为他的山河愁,而我此刻抚着这字字行行又为谁愁呢?吟着这诗句,内心竟然生出一丝庆幸,庆幸中秋有这雨遮挡住明月,遮挡着千愁万绪。 中秋夜下雨,也许是老天怜悯那些离家的游子吧,毕竟那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旅人在佳节里,尤其是在中秋团圆的节日里是何等的孤独。 记得那年在三亚,我在一个幼儿园工作。住在幼儿园顶楼的一间简陋的房间里,室内只有一张铁制的单人床,床板上铺了张凉席。两扇窗户,一面玻璃,其它没有玻璃的地方都嵌着纱窗,不知道是谁在纱窗上挂了一张挂历纸,风一吹便哗哗作响,尤其在夜里响声更甚。若逢雨夜,躺在冰凉的硬板床上,总觉得自己睡在裸露的小舟里,飘摇不定。四面风雨,八方雨声。我就在雨声里细细辨析,哪些雨是落在楼下围墙上的、哪些雨是落在院里那棵木瓜树上的、又有哪些雨是落在围墙外那几株翠竹上的,但是那雨最多的还是落在了心里,在漆黑的雨夜,声音格外清晰,吧嗒、吧嗒,…… 赶上兴致起,我会走出去。走在大街上,看着万家灯火,看着这个水墨浸染的城市,闻着海风带来的咸味。偶尔有一两声听不懂的方言入耳,我会付诸一笑,用自己的语言说一句:“你好。”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幼儿园前的小公园,那里有一片竹林,竹林边有回廊小桥,我通常站在小桥上,遥望着竹林,任雨水打湿衣衫。看雨滴落在竹叶上,一会竹林便被绿莹莹的薄雾缭绕,“沙沙”的雨声细碎而均匀。那纤纤细竹,在雨里越发娇俏可爱,枝枝叶叶虽纤细却挺拔向上,风再大只能把它折断,却无法把它压弯。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,”每每这时,辛弃疾的这句诗便随口吟出。我想我们都是倔强的,倔强到遍体鳞伤。 今夜,所幸我身处故乡,还能在我的斗室里烹茶听雨,一切都是那么温暖幸福。 注:此文年7月在《唐山文学》第期发表
散文·金色的大岭 阴沉沉的天气,让我的脚步踌躇不前,可是老朋友的呼唤又让我坐立不安。整装出发,包里多了一把伞,也多了一份期望。 雨来天低树,风润两边腮。在北方潮湿的空气简直就是老天对万物的一次奖赏。往日略显枯败的柳叶此刻格外的油亮,路边的格桑花在风里展尽风姿。车行一站又一站,它便摇曳一程又一程,金直摇得心尖软软的,再也没有一丝慵懒疲惫。 于友相约,本就是一件幸福的事,何况小镇的领导又是如此的热情。我的这些来自公主故乡的朋友们,带着雀跃,带着欢心一路高歌而来。我知道,大家和我一样,对这个只有着.37平方千米的小镇充满了好奇,更确切说是充满了敬意。 “大岭”因地处山岗上,又是镇政府所在地,故名“大岭镇”。这个位于吉林省公主岭市东北部,东与长春市为邻,北与农安县接壤,拥有人口的小镇在新中国建国70年来,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此刻,更是书写着传奇。 一条条青灰色的公路穿插在小镇与它所辖的各村落间。公路两侧黄灿灿的葵花一片连一片,远远看去似有一团团金色的薄雾在翠绿间萦绕。再远一点便是那绿浪叠起,以渐成熟的玉米散发着清香。花香草香玉米香在微风里冲击着你的四肢百骸,抓着你的嗅觉,牵绊着你的脚步,使你不能向前,不能远离,就这样呆呆地舒展你的每一个细胞,不自觉地敞开你的肺,来一次彻底的清洗。 相机、手机、凡能留下影像的工具,此刻都在闪烁。我去过百亩牡丹园,也赏过千顷郁金香,却是第一次看这葵花汇就的花海。这样的美景,这样的天然氧吧,这样的小镇谁能不爱呢? 汽车在公路上慢慢前行,我们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窗外,谁也不想错过这小镇的一景一物。 如果说刚才我们经过了飘着金子的绿海,那么此刻我们眼前便是银色的世界。一台,两台,无数台银色的轿车勾画出一个汽车王国。站在三楼窗口,收进眼里的就是震撼,我也知道,这停车场怎么会没有数字,可是我的视觉反馈给我的就是无边无际。回过头来看着远处俊杰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介绍他们的公司,我却不想去听了,还有什么比你的眼睛更真实的呢? 绿色的海洋,银色的世界,这个小镇已经让我爱上了你。 “情态温厚心络明,身姿豪爽事缘躬。仗剑不为东风舞,洁蕊自胜一品红。”处在千万株君子兰中,这些诗句就像流淌的音符,叮咚着悠然而出。挺拔、苍翠、一年四季都在书写着生命的真色。尤其百花凋零的冬季,窗外冰天雪地,收尽眼里的除了银色,便是裸露在冷风里的凸枝败叶,而此时,棚内却温暖如春,绿意盎然。傲然怒放的花蕾站在一层层的兰叶间,像骄傲的公主亭亭玉立,又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帅霸气十足。一栋大棚一室春,97栋大棚便是春满人间。怪不得这个小镇如此灵秀,原来这里善于收藏春天。 恋恋不舍告别君子兰养植基地,不禁感慨,这个小镇就是一座宝藏,处处有黄金,处处有温情。 一路走来,厂房林立,高楼叠起,工地上热火朝天。这个小镇是聚宝盆吗?怎么会有这么多商家来此投资?十几亿,几十亿的项目频频落地,今天它确实是受了春城的福泽,我更相信明天它将成为春城一道靓丽的风景。 放眼四周,绿波里萦着金光,这便是大岭,一个书写着传奇的小镇。 注:此文年10月11日在《吉林农村报》发表;年10月22日在《长春日报》发表。 散文·梦里乡关 一天一夜的辗转飞行,终于踏上这片梦中的土地。望着这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小镇,我不知所措。这真的是我的故乡吗?那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? 六十年代的小村,我家就住在村东头,再往东便是望不到边的高高低低的黑土地。大片的庄稼里住着无数个怪物,每个起风的夜里都会呜呜地冲着耳朵叫嚣。即便紧紧地闭上眼睛也能清晰地看见它们的血盆大口。那时最安全的地方便是爷爷的怀抱,十一岁的我对早逝的父母已没有太多的记忆,爷爷便是我的天和地。胆小木讷的我几乎没有朋友,只有邻居家小我三岁的小玲子成天跟在我的屁股后,像一个姐姐一样赶走一个又一个试图戏弄我的顽童。那时我便告诉自己,长大了就娶小玲子为妻。 可是贫穷让我的腰难以直起。在我21岁那年,小玲子嫁人了。嫁到百里外的城市,男人腿有点瘸,是化肥厂的工人,小玲子成了人人羡慕的城里人。在爷爷的叹息声里我狠狠地擦去泪水,不久便带着爷爷南下,从此离开了这块贫瘠的土地。我不怪小玲子,美好的生活谁不向往呢!只是心底从此有一块不能触摸的痛。 在南方的小城,车站里卸货,工地上搬砖,所有能干的活我都干过。也许老天眷顾,而立之年,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意。不再奔波,娶妻生子,日子也红红火火。只可惜,爷爷多年前故去。爷爷对故乡的眷念,落叶归根的嘱托,成了压在我心底的一块石头。生意难以脱身,总是有事情阻住回乡的脚步。诸多理由筑起的壁垒,往往会在寂静夜里的某一时刻,突然崩塌,少时留存在心底的情殇,便在此刻隐隐作痛。不知写出中华第一思乡诗的李白一生躲避归乡的原因是什么,可我却深深体会到了写出“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,”千古诗句的唐代才子崔颢那种被遗弃感。也许崔颢也说不清是故乡遗弃了他,还是他遗弃了故乡?或许两者都不是,毕竟生活存在着诸多不愿启齿的伤痛。 曾经,有那么一段时间,故乡与我只是籍贯上的文字,人身出处的一个注释。经年垂暮,走过多少名胜古迹,频频入梦的却是那个零落萧条的小村。那座低矮的草房,那雨夜里从屋顶破损处漏下的雨滴。冰凉冰凉的,每每想起,便从心底生出一股冷意。可是,不知从何时起,这冷意不在寒冷,它被岁月熬出热度。随着光阴的飞逝越发的滚烫,以至于烫得我彻夜难眠,每每遇到雨夜,更是烫得我坐立不安。 回去吧!如今也算是衣锦还乡,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。 归乡的路是漫长的。多年积攒的乡愁在随着车轮一寸一寸地被激活,故乡在我的眼前幻化。一张张脸、一座座茅屋草舍、还有小玲子一步三回头的泪眼朦胧。原来他们都那么清晰,就像人生的一段路标,在记忆深处矗立着,不管你深藏还是浅放,它都在那里,不移不动。曾经一度以为这些都被遗忘,但事实上只是你以为。 我在小镇的街头用心去寻觅,用目光去丈量,我曾经的家到底在哪里?甚至怀疑是不是找错了地方。 小镇不是很大,却整洁温馨。笔直的六排车道中间是一道修得整齐的绿植,就像一条绿蛇在青灰色街道上随着我的脚步慢慢爬行。两侧是一排我叫不出名字的风景树,金黄色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,像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。整齐的路灯一字排开,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公路北侧高楼林立,商埠、饭店、银行、邮局等罗列其中。大城市里有的人民生活配套设施这里几乎都有。路的南侧除几座二层商铺外,便是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院落。看见那似乎有些熟悉的建筑,不禁心头欢喜。于是便顺着那一砖一瓦在脑海里搜寻,可是怎么努力也无法同记忆力里的小村联系在一起。那从记忆深处蜿蜒而来的是一条黄褐色的土路,坑坑洼洼伸向远方,随着尘土与泥泞又回归记忆深处。 街头询问了两个年轻人,当听到“大岭村管所”几个字,都茫然摇头。这么多年刻意保留的乡音在这里一张嘴还是让人家怀疑是外乡人,心里顿生酸涩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我相信贺知章一定遇到了我此时相同的遭遇。 无奈走进派出所,热心的民警告诉我,这里早已由村变成乡,再由乡变成镇,现在叫大岭镇,这里的人口已经增加到3万多人。还热情地帮我联系到了小玲子的爸爸。是的,现在除了小玲子一家我不知道我还能投奔谁去。 当年四十几岁的汉子,如今却已是两鬓如霜。幸好身体健康,八十多岁的人居然满面红光,看见我的瞬间便泪眼模糊,我的心中无比酸涩,这一家人可能就是我的故乡吧。 一路上他不停地指着周围的变化说道:“这个是新建的小区,就是你家东边那片玉米地,现在都开发成住宅小区了,再往东的那些厂房有的是汽车厂建的,有的是回乡大学生建的,那里还有一些生态园。因为与长春相邻,大岭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很快,年轻人很多都在汽车厂上班。”当然我们谈得更多的还是小玲子,得知她结婚七年时,因为性格不合离婚了,再也没找,带着孩子种菜维持生活。听着老人不停的叹气声,我不由得心里一痛,手指下意识地捏了捏兜里的钱包,暗暗想,小玲子,也许这次我该为你做点什么了。可是老人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有些颓败了。 “现在她和儿子一起弄了一个果蔬生态田园,都种些纯绿色蔬菜,一年四季给附近各大市场、超市供货,生意相当红火。我也整天跟着忙活。” 清晨的大岭镇被阳光拥在怀里,像被渡了一层金子。现在与省城长春同城管理,人们的生活早就融入到大都市里了。这里到处充满着希望,与我梦里那个贫穷的故乡差得不只是千里万里了。我为故乡崭新的变化而高兴,同时也为那远去岁月而伤感,我的故乡在梦里有了新的模样。 注:文年9月在《春风文艺》发表。 小说·蒜嫂往事 关上院门和房门,张桂枝心口还是怦怦跳。昨夜去哥家,哥嫂要出门旅游,托她把大狗黑毛牵过来照看几天,反正她跟这狗也熟。黑毛冲新主人摇尾巴,桂枝就把它牵回灶间,喂些食物,她顺势坐在灶台上发呆。 刚才从县城办完事回村,她远远地感受到身后几个男人的目光,风儿吹过,听到二棍几个怂恿李富:“你那眼珠子瞪烂了顶什么用?有本事,今黑天把她弄了。我请,这几位都算。” “说话不算呢?” “王八蛋!” 好恼啊。打自家爷们车祸走了,桂枝也不是没考虑改嫁的事,结婚才两年,连个孩崽都没有。本来看着李富人长得周正,做事也像个爷们,可这不争气的东西,拿俺当骰子耍了,这要是让瞎话婆们传扬开去,往后她怎么活人?桂枝决定,打明天起,跟李富见面绕着走,人不能没骨气。 黑毛吃饱了,再次冲她摇尾巴。 桂枝拍了拍黑毛的脑袋,没心思理它。她转身剥蒜。晚饭拌点凉菜吃吧,这几天上火,什么也不想吃。肩胛处的牛皮癣又犯了,抓心抓肝地刺挠,她一边剥蒜一边抽空用拳头去擂那痒处,心里边骂着李富那个坏种。等醒过神儿来,发现两头蒜都剥完了。 这工夫天已黑透,桂枝捣着蒜泥想心事,忽然听到院门不对劲。贴门缝一望,院门让人打开了,李富这个天杀的已进到了院子里。刚才几个臭爷们的话又在耳边响起,这可如何是好?桂枝急中生智,知道那李富不吃葱蒜,尤其沾蒜就呕,她抓起一把蒜瓣儿就填进嘴里猛嚼,然后,又抓起一把蒜泥抹在牛皮癣上,顾不得钻心疼痛,她猛一把拉开房门就冲了出去。 李富堵在房门口呢,见鱼儿轻易碰网,扑过来一把抱住桂枝就亲,嘴没凑上,就听“哇:的一声,吃下肚的晚饭呕在了一侧。 黑毛这条哑巴狗不会叫唤,却知道护主,见有人欺负主人,它从背后把爪子搭在主人肩上,脑袋伸过去,冲李富张开血盆大口。那狗站起来比李富还高,吓得李富“妈呀”一声,掉头就逃,不小心撞在院子一边的摩托车上,连人带车倒在一起。桂枝看到他顾不上伤痛,爬起来逃出院外,门外响起一阵男人的哄笑。 叫桂枝猜个正着,傍黑那几个男人正守在院外看热闹呢。 桂枝忙把黑毛安抚住,真咬坏了人不是玩的。紧张过后,这才感觉牛皮癣沾上了蒜泥那种钻心的疼啊,她刚想把蒜泥抹去洗净,可又发现,这种疼比痒还舒服些,于是,凉菜也不拌了,她索性把蒜泥均匀地涂在了痒处。 奇怪,只抹了两三回,那癣褪掉一层皮,好了! 这样顽固的病痛,差不多把大夫都麻烦遍了也没根除,偏巧一堆蒜泥就解决了苦痛。桂枝高兴得手舞足蹈,她甚至暗自感谢起李富来,不教他那天夜里骚扰,她哪里来的这办法! 打这时起,桂枝上了心,暗暗琢磨如何用大蒜给人治病,经过研究,她添加了几味中药,专给人治皮肤病,效果不错,她也多了些收入。 这年大蒜价格跌得吓人,好多蒜农伤透了心,都决定改种别的庄稼。桂枝不这么看,她想,本地大蒜蒜头大,颜色白,皮厚不散瓣,存放时间长,跟别处的大蒜比较,一尝就知道口感明显好得多,这么大个国家,主要是没宣传好,许多消费者根本不知道,如果宣传得好,肯定是抢不上手的。桂枝灵机一动,把丈夫车祸的那笔赔偿和治病赚的钱全拿出来当定金,挨家挨户宣传,你们只管继续种,咱们签合同,我包收购,赔了你们不用负责。 见了定金,再少也是现钱呀,蒜农们乐呵呵地签了协议。 桂枝长出了一口气,关上门对着丈夫的遗像祷告:我不但是为了自己,也赌的是家乡大蒜一口气,这一注若是押错了宝,我很快就去找你做伴去了。 转过年,桂枝手下的蒜农大蒜获得丰收,更令人欣喜的是,价格比前几年最贵时还提高了一倍!桂枝对蒜农们说,别看咱们签的收购价有合同,如今涨价部分五五分成。说着,指挥装车拉往县城。桂枝边带动乡亲们种蒜致富,同时还开设了蒜疗馆,聘请专家研究开发大蒜的养生功效造福乡里。她的侠义之举赢得了一片欢呼,蒜农们不分长幼,都称她“蒜嫂”,大伙异口同声,这样的好人,咱不选她当村领导,那岂不是瞎了眼! 再说李富,憋足了劲,要在蒜嫂面前争回面子,见桂枝转包大蒜他也紧跟,虽然数量没蒜嫂的多,但是,他涨价的部分全归自己,估计差也差不了多少,看那娘们儿明天不对他另眼相看,到时候,当众献束玫瑰,还愁连人加蒜不都归了他李富。 哪知道把蒜卖到县城,收购方直接把大蒜转到了蒜嫂公司加工包装,一打听,明白了,原来人家桂枝注册了蒜嫂品牌,并把它宣传到了附近好多城市,同样的大蒜,蒜嫂的品牌蒜因为检验把关严格,质量信得过,价格要高出一倍,并且赢得了好口碑! 回到村子,李富见蒜嫂正跟蒜农们宣讲营销新理念,动员乡亲们入股她的公司,他挤进人群,眼泪汪汪地叫了声:“蒜嫂……不,张总,我口服心服了。我愿意归顺你,给你当个门卫中不中?”说着,掏出一头大蒜,填进嘴里,喀喀喀嚼得山响,辣出满脑门子汗。 桂枝早就听说,为了跟她保持一致,这李富天天练习吃大蒜,如今习惯了,一顿不吃,饭菜都没了味…… 眼见他这般虔诚,蒜嫂眼圈一红:“李大哥,你说你这是何苦……”注:此文年12月在《南叶》第,期发表:同年在众艺杯戏剧曲艺作品征文大赛中获二等奖。 、 端午节 日暖江堤翠笼烟, 龙舟竞技水波旋。 离骚韵唱思家国, 天问音留解惑笺。 粽叶含香香万里, 酒魂赋醉醉千年。 今朝笑慰神州好, 风顺帆高正向前。 注:此诗获天津市“和平杯”三等奖 送别 放歌一曲为卿狂,最美离人身上装。 薄酒杯温千里路,楼头月冷半纱窗。 谁人柳下吟低语,那个庭前问短长。 溅落星辰惊爱鸟,长亭梦断几柔肠。 注:此诗年在《长春协商新报》发表。 桑榆文学编辑部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yipinhonga.com/yphxx/724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植物激素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最全资料
- 下一篇文章: 赵蘅传承不息,精神不死